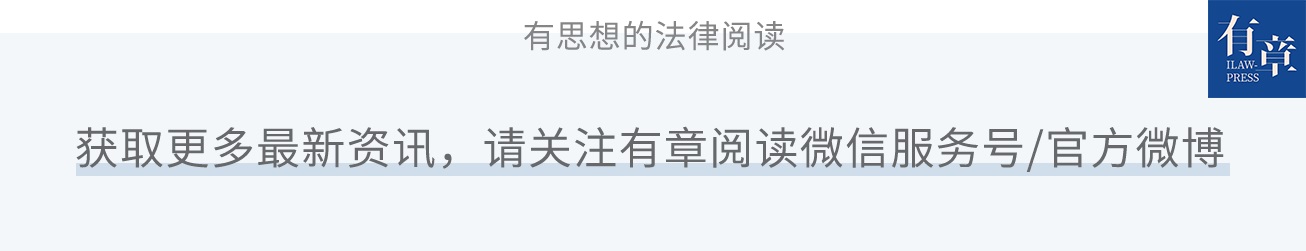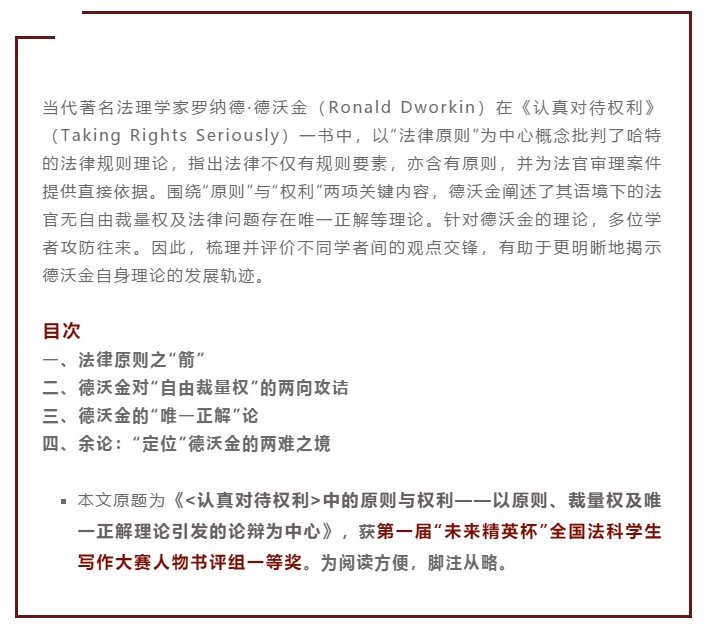

法律原则之“箭”
如果将法哲学研究比喻成马拉松,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出色的传承者和接力者无疑是哈特(H.L.A.Hart),承接边沁(Jeremy Bentham)以及奥斯丁(John Austin)以降之分析实证法学传统,同时开启另一别样丰富讨论之先河。如果论者谓哈特树立起最宏伟的分析实证法学标靶,论者无疑也会承认,射向这个标靶的最犀利的一只箭镞来自德沃金。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在法哲学的论争中,哈特的在场,乃至于无法“退场”,德沃金一人厥功至伟。
(一)作为“标靶”的哈特
在《法律的概念》中,哈特提出了“法律规则论”作为一种对法律自身的描述。凭借对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批判,哈特指出,由于现代社会并不存在奥斯丁所谓的主权者,而且法律和命令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故法律并非是主权者的命令,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毋宁由规则构成,且这里的规则包括由基本义务规则构成的初级规则,以及由承认规则、裁判规则和变更规则组成的次级规则。
同时,哈特并不苟同形式主义和规则怀疑论两种学说,因为前者认为法律可以精准地涵摄所有法律事实和案件,法官只能够依据现有法律审案,故过于僵化和理想化,而后者却对法律规则报以巨大的怀疑,甚至认为法律是“对法官将要做什么的预测”,故会导向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简言之,于哈特看来,在美国的法理学中,前者是“美梦”,而后者是“噩梦”。
基于此,哈特认为,由于(法律)语言自身存在模糊性、立法者认识的局限性而无法制定出规制未来所有情形的天衣无缝的法律等原因,法律文本自身便会存在开放结构,也正因此,法官在审理当前法律规则无法涵摄的疑难案件时享有自由裁量权。一个社会的法律的效力最终并非来自习惯,而是来源于承认规则。
然而,德沃金却不赞同上述法律理论。他把对哈特理论的批判作为基础进而建构起自身的法理学。通过对若干具体法律案件的研究以及对概念理论的分析,德沃金得出如下结论:
法律体系除规则以外,还应该包含原则与政策;原则与规则的区别在于,(1)规则全有或全无地适用于法律案件,即“假如给定了规则所规定的事实,要不规则有效而必须接受它所给定的答案,要不它无效而对判决毫无影响”,而且,一旦某条规则在某个具体的法律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那将会得出确定之结果。而原则却无此特征,因为不同的原则之间会发生冲突和竞争,故当某一项原则适用于法律案件时,并不会确保一项特定的结论,而只会指向某个方向,或为判决提供某种证立,亦即哈特所作出的概括——“非决断性”,处理案件的法官此时必须衡量相互冲突的不同原则以适用于该案件,以及(2)法律原则具有重要性或分量之面向,而规则却无此面向;法官在很多时候也是将原则——而非规则或政策——作为裁判的依据;承认规则从根本上来说无法鉴别法律原则,因此,法律原则无法被纳入哈特所描述的法律规则体系当中。
无疑,德沃金提到的法律原则对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产生了冲击;而且在哈特看来,法律原则在德沃金对其法律规则理论的所有批评中亦最为著名。
(二)争论再起
应当说,德沃金的法律原则理论不乏信众,却无法彻底“服人”。据笔者有限的阅读,在与法律原则有关的问题中,核心议点当属原则与规则的区分。德沃金的两点区分被新加入到争论中的拉兹(Joseph Raz)和捍卫自己理论的哈特所反驳。
1.规则与规则的冲突
拉兹不赞同德沃金所认为的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冲突及其区分,他指出:(1)不仅是规则与原则之间会发生冲突,规则与规则之间亦存在冲突之情形,因此(2)在此种情形下,法官必须衡量相互冲突的规则以作出裁判,所以规则也具有了原则所具有的“分量性”,也是在“指向”而非“决定”案件的结果,所以德沃金作出的规则与原则的上述两点区分便不复存在。针对以上观点,德沃金在回应时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式。
首先,拉兹设想,在道德议题中,某人会事先接受两条规则以指引自己的行为,而在某些具体状况下,这两条规则会相互冲突,而此人这时必须衡量两条中的一条以指引而非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在这一道德困境及随之而来的道德选择中,道德规则指引却没有决定某人最终做出何种行为。
但是,德沃金认为,拉兹对道德议题给出了错误的描述,没有看清其深层次的内在逻辑。他对此种观点反驳道:大多数道德议题不是拉兹设想的这样,而是一件针对某些行为过程合不合乎某项道德提出支持或反对的理由的事务,即给出理由以证立或反对某具体行为过程是否符合某项道德。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出现拉兹所描述的那种对道德规则进行选择的情形,那么,拉兹上述的前两点反驳便不会成立。
但是,也可能存在当事人被迫面对两条道德规则而加以选择的情形,此时,德沃金认为,这其实是两条原则而非规则之间的冲突,因为处于此种情形的当事人实际上知道,没有一条道德规范可以完全压倒另一条,他必须衡量其重要性以做出选择,此时用道德原则来描述其最终选择的道德规范是更加准确和有说服力的。
除去上述两种情形,由于某人可能会对两条道德规范持有绝对的信念,因而依然可能存在两条道德规则(而非原则)相互冲突的情形(尽管这颇为罕见),而此时如果还以原则而非规则来描述这两种规范就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描述忽略了此人对规范所持有的信念的绝对性,而此种信念会决定而非指引其做出何种行为。
但是,德沃金反驳道,其法律原则理论并未排斥规则之间也会产生冲突;相反,规则产生冲突的情形是一种“紧急状况”,而此时必须做出抉择以选择其中一条规则而修改另一条,或对两种都进行修改,这样,被修改的规则就会变成原则。例如,在“二战”中,假设有位无辜的村民甲为自己设立了“不得撒谎”与“必须信守承诺”这两条道德规则,某一天甲收留了一位犹太人,并向其承诺不会告诉别人他的存在,随后,有位纳粹士兵询问甲的家中是否有犹太人,显然,甲此时必须在这两条道德规则之间作出抉择;假如甲最终没有向纳粹士兵暴露犹太人的存在,那“不得撒谎”这条规则就被修改为“原则上不得撒谎,但在为了救人的紧急状况下可以撒谎”这项原则。
因此,拉兹上述两种观点并不成立。笔者认为,德沃金针对拉兹两种观点的回应的重点在于对观点(1)的回应,因为拉兹对道德规则发生冲突作了错误的描述,故观点(1)就不成立,既然如此,立基于该观点的观点(2)也自然缺乏说服力。
2.规则的自体属性
所谓原则与规则之争,实由规则而起,而规则自体的属性,或言“规则的特征”实为论争之中心,针对前述德沃金的法律规则全有或全无(all-or-nothing)的观点,拉兹进入了“中心”。
他指出:规则与原则发生冲突这一事实会消解规则的“全有或全无”之特性,因为法官在这种情形下需要衡量彼此间相互冲突的原则与规则以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并据此作出裁判,既然如此,那么就必须赋予或预设规则存在一定的分量,否则就不可能进行衡量,因此,规则此时并非全有或全无地适用,而是依然发挥一定的作用。
针对此种观点,德沃金认为,他“其实错误地诠释规则与原则的互动”:在某一法律案件中,如果法院决定根据一条原则以推翻先前的判例所形成的规则,那么针对此种情形,我们就不能将之理解成是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冲突,而必须理解为原则与规则背后的原则(如遵循先例原则)之间的冲突,而法院此时也必须在两条原则之间做出衡量并选择其一,“因而,‘法院比较规则与规则或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分量’这种说法造成误导。”
哈特似乎借鉴了上述拉兹的观点,并且顺着德沃金对拉兹的反驳而继续深入。他认为,德沃金将原则与规则的冲突解释为原则与规则背后之原则的冲突无法自圆其说:此种解释更能说明规则不是全有或全无地适用,以及原则并不具“非决断性”之特征,因为此时规则的效力已经被支配其自身的背后的原则所取代,规则实际上并不在场,故规则无所谓“全有或全无”,而决定案件结果的也自然是规则背后的原则而非规则本身。
的确,笔者认为,德沃金将规则与原则的冲突解释为规则背后的原则与原则的冲突的做法,似乎意味着是在主动抛弃他自己为规则所立下的第一项特征。哈特进一步指出,即使是非常清晰的规则也有可能获得新的诠释,而此时原则又会为这种新的诠释提供证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规则也不一定会决定案件的结果。这种情形在美国宪法史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特别是在司法能动主义盛行的沃伦法院时期。
比如,若将1954年的布朗案作为一个分水岭,便会发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特定条款(法律规则)在前后分别作出了不同解释:在此案之前,该法院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的含义解释为“隔离然而平等”;而在此案中,九名大法官却一致判决“‘隔离然而平等’这个原则不适用于公共教育领域。”
在上述针对规则“全有或全无”之特征展开的论辩中,学者们将各自的思索推向顶峰,亦似无人在你来我往中拔得头筹,但论辩之意或不在此,而为法哲学研究本身提供不可多得的思想“质料”应为论辩的真谛,或说所有的论辩都理应如是。
另有一点值得关切,即必须仔细区分如下两个问题:德沃金对于规则与原则的区分是否准确及有效,以及德沃金提到的原则这类规范是否对法实证主义产生了冲击。之所以作如此区分,是因为即使前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也不会影响对后者的回答。德沃金对于其原则理论做了“兜底性说明”:即使无法准确区分原则与规则,其所主张的那类规范(即原则)也将对法实证主义产生冲击。
其论据在于:首先,在逻辑上区分规则与原则可能为假,但这不代表两者间没有实质性区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原则这类规范最终无法由承认规则进行鉴别,对法实证主义的理论框架造成了冲击。
(三)与原则“并行”的政策
1.原则与政策的界分
除了原则与规则的区分,与原则紧密相关的另一问题亦不容忽视,即原则与政策的区分问题。已于前述,原则之外,德沃金还提出了以期更加精准地解释法律问题的“政策”概念,并对原则与政策作出如下区分:某项规范,如果是为了达成某个集体目标,那么此规范即为政策,与之相应,以通过说明让某个个体或团体获益有利于社群整体的集体目标之方式,来证立某项政治决定,此时所依据的是政策论据;某项规范,如果其效力源于正义或道德亦或权利,那么这项规范则为原则,与之相应,以通过说明某人或某团体享有获得利益之权利的方式,来证立让该人或团体获得利益的政治决定的论据为原则论据。
简而言之,原则(论据)所关注的是“权利”或“正义”,而政策(论据)关注的核心是“目标”。与此项区分紧密相关的德沃金的另一观点亦不容忽视,即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典型地将原则(而非政策或规则)作为判决的依据。
对上述原则与政策之区分的反对是格林瓦特(Kent Greenawalt)提出以下质疑的前设:法官并不像德沃金所认为的那样,通常依据原则论据为其判决提供证立,相反,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常常将政策论据作为其判决的依据。限于本小节的主题,笔者将把焦点放在前设本身(即原则与政策之间并不存在德沃金所言的区别),而非格林瓦特的质疑;实际上,解答前者也实质上回应了后者。
德沃金首先警告,不可将原则论据与政策论据之间的区分混淆为后果性权利论据与非后果性权利论据之区分;务须清晰地区分后果性权利论据与政策论据。因为,原则论据既包含非后果性权利论据,亦包含后果性权利论据;后果性权利论据无法等同于政策论据。
随后,他将此种分类用作分析具体的法律案件:假设A与B两人所在土地相邻,B在其土地上开工厂的行为有损于A对自己土地的使用,A向立法机关主张制定要求B停止其开设工厂之行为的法律。
在此种情形下,B为了说明A没有要求立法机关通过此类法律之权利,其可能有各种依据:首先,B可能主张A这样做会损害其开设工厂以经营企业并赚取利益的权利,此为与A相竞争的权利论据,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原则论据;其次,B可能主张A的做法会导致其所在社区失业率上升这种后果。在后一种情形中,若立法机关采取B的主张,那么此时B的依据虽然表面看由于诉诸后果因而是政策论据,但实际上,它是原则论据,因为此时该论据完成了两项任务——“驳斥A请求通过制定法的权利主张,也同时驳斥‘就算A无权主张,制定法也是可欲的’这种独立政策论据。”再根据之前给出的对原则论据的阐释,此时该论据达到了证立当事人一方是否有权利的要求,所以,它是原则论据。
最终,德沃金抽绎出区别原则论据与政策论据的标准与方法:区分原则论据与政策论据的关键之处是要关注该论据要试图回答的两类问题——“当事人有没有要求某些政治决定或判决的权利”和“有没有有力的政策性基础”,如果该论据是在回答前者,那么它就是原则论据,“尽管这项论据在细节上可能是彻底的后果论式的”。他分析道,格林瓦特对他自己举出的法官依据政策证立判决的例子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因为据上述标准,在这些案件中,法官实际上是在依据原则为其判决提供证立。所以,格林瓦特对原则与政策之区分的质疑表明看似合理,但实则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稍加总结可知,德沃金的回应主要包括两点,即区分后果性权利论据和政策论据,以及剖析该论据是否是在回答“当事人有没有要求某些政治决定或判决的权利”这类问题。某项决定或判决的依据是否诉诸后果,与该依据是原则还是政策无关;不能仅仅因为某项判决依据与后果有关联,就推导出该依据是政策。
2.“琐碎主张”与法官的判决
然而,上述对原则与政策作出的细微区分已为格林瓦特所预见,并且提出了德沃金必须予以解决的另一棘手问题:如果如此随意区别原则与政策,那么将导致该区分琐碎且微不足道,也因此,“法官典型地运用原则而非政策证立判决”这项指示不会对法官的裁判行为产生任何影响,法官在实践中还是会依据自己的方式裁判案件。此种“琐碎主张”似乎具有某种虚无主义的倾向,但无论如何,德沃金必须论证原则或政策的要求究竟是否会对法官的裁判产生影响。
德沃金首先指出这种形式的主张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一件事实,即在原则或政策的背后,法官自己会采取某种相对固定的道德理论或判断当事人享有某种权利的权利理论,而正是这种权利理论决定了原则或政策的要求是否对其裁判行为产生影响,以及影响是否不同。既然如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考察:(1)法官普遍会持有哪种形式的权利理论,以及(2)这种权利理论是否会决定原则或政策的要求对法官产生实质性的不同影响。
对于问题(1),德沃金首先为权利理论做了分类,一种是后果论式权利理论,另一种是严格的本务论式权利理论(deontological theory of rights)。他指出,采取后一种理论的法官会直接排除任何政策论据,而采取本务论原则,而并不会给予政策哪怕一点关注;但是,由于此种理论过于极端,不会将任何后果纳入考量,而少为法官所持有。紧接着,他又对后果论式权利理论进行分类,共五种类型:第一种立足于行为功利主义,二、三两种立足于规则功利主义,最后两种拒绝任何形式的功利主义而只考虑某些后果。若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德沃金在这里区分的五种类型的后果论式权利理论,就会发现,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两种——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式权利理论和非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式权利理论。
前种理论认为,某种行为或规则必须要产生功利主义者要求的最大效益,此时才能产生相应的权利;后种理论认为,某些后果应当纳入考量,但某些权利(如获得他人尊重的权利)并不取决于行为或规则是否达到最大效益,而是本身就存在着。简言之,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式权利理论主张权利仅产生于达到最大效益行为或规则,而非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式权利理论则主张某些权利本身就具有价值,同时考量某些后果。德沃金认为,法官(至少是在英美法系中)会普遍持有后者。因此,对于问题(1),德沃金的回答是:法官普遍持有非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式权利理论。
问题(2)会随着问题(1)的回答而迎刃而解。既然法官普遍主张非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式权利理论,而这种理论既关注某些后果,又强调某些权利本身的价值,因此,当法官被要求以原则作出判决时,他会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权利,而当其被要求以政策作出判决时,则会更加关注裁判的后果。
简言之,笔者认为,法官普遍持有的这种非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式权利理论,相当于一个位于原则或政策的要求与裁判结果之间的桥梁或中介,当法官在接到原则与政策的不同指令时,他/她会作出不同反应。由此可见,当法官持有该理论时,不同的要求会引导其做出不同的判决,故“琐碎主张”并不成立。格林瓦特的“琐碎主张”的一个关键缺陷就在于,它忽略了法官会持有特定的权利理论这一事实。
然而,据笔者分析,上述德沃金回应“琐碎主张”的论证过程带有直觉性的意味,即他只是假定法官会普遍持有后两种较不极端的权利理论,但并未对此项假定展开详细论证。笔者对这一假定不禁要提出反例:倘使确实有某法官持有前三种权利理论,那以原则和政策作为指示就不会对该法官产生影响。
当然,德沃金对这种假定并未给出详细论证的原因或许在于,后两种权利理论是英美法律人(特别是法官)的共识,在这一点上,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人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隔膜。由是引发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研究诸多法理学家的论辩时,要区分三个不同的维度——“我们眼中所认为的他们争论的焦点”、“他们争论的焦点”以及“他们对特定问题应该争论的真正的焦点”。抑或追问道,某一个问题是否确实存在一个或几个真正的焦点?最后一个维度最难把握,因为这涉及到对文本或某位学者的误读与否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能够达到对文本或学者最客观的理解,这本身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或者,可以继续追问:研究方法上的客观是否一定能够达成研究结果之客观?达到对某一文本或学者的“客观”或“正统”理解何以可能,以及这种“客观”或“正统”理解有无存在之必要性?非误读的“客观”或“正统”理解是不是在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抑或流于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误读”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能够使得学术创新与繁盛成为可能?
德沃金对“自由裁量权”的两向攻诘
(一)以原则为中心的反向论证
德沃金在提出(法律)原则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另一项“主张”——自由裁量权:在任何法体系中都存着未受当前法律所规制的案件,而法官针对这种案件会创造新的法律规范,当然,既存的法律规范也会约束法官的行为。
那么,在判决受到原则影响的情况下,法官是否真的像哈特所说的那样拥有自由裁量权?为解决这一问题,德沃金首先提出了预设性观点,即原则支配着法官的裁判。然后,他通过反向论证,即逐一反驳法实证主义可能提出的针对该预设的批评性观点,以证明这项预设为真;既然此项预设为真,即原则支配裁判,那么,在规则不起作用的案件中,法官会受到原则的实质性支配而无自由裁量权。因此,要论证法官是否拥有自由裁量权,其关键之处在于审视法实证主义对于“原则支配裁判”这项观点的反对理由是否合理。
第一,法实证主义者可能主张,原则不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也不会产生义务。这种反对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由原则的特性(即在上文提到的分量性与非决断性)推导出原则无拘束力。德沃金认为,如果某项原则存在且能够被适用,法官就必须予以考量,这是法官的责任,而如果无视其存在,案件当事人乃至普通大众都会指责法官没有尽到职责。因此,原则的非决断性并不代表原则无拘束力;原则在实质上会对法官裁判行为起到拘束作用。
第二,法实证主义者也可能主张,即使上述第一种反对观点是错误的,即承认原则有拘束力,但原则“不能决定特定结果”。
针对此种观点,德沃金首先承认,某些原则肯定无法如同规则那般能够“直接确定”或”支配”案件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原则不同于规则,因为它是为判决提供某个方向而非直接确定结果,而且,当结果改变时,规则就必须被更改或废除,而原则依旧会完整无缺地留存下来,在规则不适用时依然起到指导案件的作用。所以,当无法适用规则于特定案件时,原则因在实质意义上发挥着作用,所以最终依然会决定或支配判决。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要在规则和原则两种不同的语境下理解决定一词的含义。
其次,当法官面对多个可以支配结果的原则时,“似乎并没有任何理由认定……非得衡量原则的法官就因而享有裁量权”,因为,就像选择适用不同的规则一样,对于不同的原则,如果法官“相信”某项原则适用于该案件,那么他/她此时便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适用此原则,因此法官并无自由裁量权;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认为法官拥有自由选择原则之裁量权,那么,在法官衡量不同的规则的情形中,就必须认为其也拥有自由选择规则之裁量权,而这样做相当于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在自掘坟墓,因为根据这一概念,当规则有明确规定时,法官并无自由裁量权。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法官可能在适用原则时出现了选择上的错误,但是,选择适用规则也同样可能出现错误;不能因为法官可能出现选择上的错误就认为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
最后,在做出判决时,即使在规则并无明确规定的疑难案件中,法官也“必须”考虑各种因素,而非自由甚或任意做出判断,因此,从此角度来审视,法官亦无自由裁量权。
第三,法实证主义者还可能主张,“原则算不上法律,因为它们的权威,甚而它们的分量,天生就有争议。”针对此种观点,德沃金长文以应。
首先,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法实证主义理论框架中“承认规则”这一基本概念。承认规则是一种标准,据此标准,“可以判定哪些规则属于、哪些规则不属于法律体系”,并且赋予规则以效力与权威。但是,根据德沃金的分析,由于在规则的背后起到支配性作用的是原则,而非哈特所说的承认规则,所以,原则不仅会消解掉承认规则存在的正当性,而且会减损后者的实质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承认规则无法鉴别原则,即承认规则这项判准无法适用于原则。既然如此,法实证主义者在其理论框架下就不能随意断定原则的权威或分量存有争议。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如果因为原则的分量有争议就断定其无法决定判决,那么这将会导向一种法律虚无主义之倾向,因为,由于承认规则最终由社会的惯习、实践等一系列因素组成,因此该判准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故如若接受上述观点,通过类比也可以得出结论:承认规则的分量与权威也存在争议,因而无法鉴别一个社会的法律。换句话说,原则本身可能存在争议,但由此一事实不能够推导出原则无法支配裁判。
其次,在英美法系中,法官推翻先例和固有的规则的案件时常发生,如果此时法官真的享有强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而不受到任何其他规范的约束,那么法官不就无法无天了吗?因此,德沃金主张,我们必须认为,存在着约束法官的规范,而且这种规范决定了法官在什么情形下能够推翻先例或改变固有的规则,在什么情况下又不能这样做。这种规范只能是原则,因为,当持有某种原则以为其判决提供证立时,法官才有理由推翻先例;即使在遵守固有之规则的情形下,法官依然在遵循原则,因为此时他/她必须考虑“立法至上”以及“遵循先例”这些原则。因此,可以说,原则最终对于约束法官的行为起到“兜底性”的作用。
通过对法律实证主义上述三种反对“原则支配判决”之观点的逐个反驳,德沃金最终得出结论:原则在实质上支配着判决,因此,法官并不享有自由裁量权。
仔细检视上述证成法官无自由裁量权的看似冗长的论证过程会发现,德沃金的论证思路是很巧妙的。他没有直接回答“法官有无自由裁量权”这个问题(问题①),而是先引用原则这个概念问到“原则在具体案件中是否能支配判决”(问题②)。然后,其焦点集中在问题②。对于问题②,德沃金也没有给出正面回答,而是通过反向论证得出答案,即通过“反驳”法实证主义者认为“原则不能支配案件判决的观点”而得出了对问题②的肯定回答,进而推导出对于问题①的否定回答。
除此之外,德沃金还提出了其他针对自由裁量权的批评性观点以支持其上述结论:
(1)法实证主义认为,在现有规则无法适用的疑难案件中,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必须创造新的规则与权利以适用于该案件。而德沃金认为这种观点是对法官司法过程的错误描述;实际上,即使在疑难案件,法官也是在发现并适用已有的权利,而并没有创造新的权利。
(2)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创制新的法律违背了民主原则。法官并非民选而产生的官员,因此不能独断地创制法律规则。运用原则作出裁判则会避免此类问题。
(3)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是不正义的,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之原则:如果创制新的规则适用于当前案件的当事人,那将会造成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突袭。而运用原则作出判决则不会产生突袭,因而也不会造成不义。
(二)以权利为中心的正面推理
针对上述德沃金以迂回进路否定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哈特与格林瓦特发动进攻,德沃金此处进行正面回应。
格林瓦特的主要论点是:如果被广泛地认为是“适当”的判决或“令人满意地履行了司法职责”的判决存在一个以上,那法官就有选择其中一项判决的自由裁量权。对于这项论点,由于其使用的语词(“适当”和“令人满意地履行”)存在模糊性,德沃金首先对其做出了两种诠释或理解:(1)当人们广泛地认为,案件双方都没有获得胜诉判决之权利的时候,亦即当从当事人权利的立足点出发,两种判决都同等正确的时候,存在强意义的自由裁量权;(2)当人们广泛地认为,“追求关于当事人权利之正确判决的、诚挚且负责任的努力,可能会达成一个以上的结果”的时候,强意义的裁量权就存在。
德沃金指出,对于格林瓦特上述观点的诠释,诠释(2)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它成立,那就相当于说,通过对各种因素的考虑,尽管当事人有权获得其所追求的判决,但法官仍然享有自由裁量权。倘使当事人有获得胜诉的权利,那法官就必须据此裁判,而没有商量的余地,亦不存在自由裁量权。
因此,只能将诠释(1)作为对格林瓦特主要论点的理解。针对诠释(1)(亦即格林瓦特的观点),德沃金首先假定它是正确的,此时法官是否拥有自由裁量权将取决于法律人是否认为双方都没有获得胜诉判决的权利这一事实,如果这种事实出现,那法官就拥有裁量权,而格林瓦特的观点也就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事实的出现十分罕见,因为在具体案件中,确实很少有法律人(特别是作出判决意见的法官)会认为自己对当事人权利的意见是错误或次等的,他们往往都会坚信自己的意见才是正确的。
既然这种事实很少显现,那立基于此的诠释(1)就是不合理的。再者,最重要的是,德沃金指出了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没有区分“认为法官享有裁量权”(或“对法官享有裁量权持有信念”)与“法官确实享有裁量权”,亦即没有区分信念与事实。
如此一来,即便法律人广泛地“认为”两种判决都正确,那也不能说明两种判决“在事实上确实”都正确,即由前者无法推导出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因此,德沃金最后指出,格林瓦特的主张必须修改成如下叙述才能够成立:“如果两个判决确实(不只是被认为)同等正确,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两造都没有获得特定判决的权利,裁量权就存在。”
哈特针对德沃金上述第一种批评性观点,指责他没有看清司法过程之事实,因为说法官的判决是在发现而非发明新的规则或权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首先,从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法官的观点来看,当前法律存在着无法规制案件具体情形的漏洞,而此时填补法律的漏洞是法官的责任,不应该逃避;法官不仅仅是立法机关的“传声筒”。其次,法官在上述漏洞的情形也并非是在无约束地做出裁判,而是运用了类推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要求法官必须衡量先例所具有的分量以及各种因素,从而会削弱法官造法的成分。
哈特对于德沃金的第二种批评性观点的反驳从三权分立制度展开:虽然将造法的权利让渡一部分给司法机关会在一定程度上违反民主原则,但是这样做会提供许多便利以完成立法机关所无暇顾及的具体个案,而且,相比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将部分造法的权限委托给司法机关所造成的危害会更小,因为司法机关既没有军事权,也没有财政权。
除此之外,笔者也认为德沃金的这种批评性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公民们不仅需要警惕政府权力的滥用,也必须警惕多数的暴政,而将部分造法的权利交给司法机关,特别是拥有独立地位且终身任职的法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对民主的激情与盲目发挥良好的冷却剂的效果,因此,牺牲一部分民主也是值得的。
对于德沃金第三种批评性观点,哈特认为核心问题在于他对于法溯及既往的不正义性做出了错误的理解。哈特承认,溯及既往的法是不正义的,但其不正义性应该在于“违反了行为人在行为当时合理的期望,这个期望就是,行为的法律后果乃是按照行为当时已经存在并被知悉的法律来决定”,但是,在疑难案件中,此种不正义并不存在,因为此时缺少清楚的既定规范为行为人的期望提供正当性,也就是,此时行为人已明确得知其行为缺乏法律的规制或缺乏明晰清楚的法律的规制。
(三)新的视角
笔者认为,要检验德沃金的“法官无裁量权”之主张是否合理,可以借鉴罗尔斯(John Rawls)的反思均衡法(reflective equilibrium)。在法律领域当中,大可如此表述这一方法:某种法律理论是否合理,取决于①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合理地描述/说明了某一地域的法律实践经验,以及②它能否为该地域之法律实践提供证立(justification)。
首先,如前所述,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当审理特定疑难案件时,很少有法官认为自己的裁判结果要比其他法官的裁判更不合理,因此,法官往往认为自己作出的裁判就是“正确答案”,是故“法官无裁量权”这一主张(法律理论)能够符合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其次,“法官无裁量权”意在说明法官并非肆意地做出裁判,故法官的裁判会因之更具权威性与合法性,因此,它能够为法官的裁判行为提供证立。
综上,笔者认为,德沃金的“法官无裁量权”之主张能够满足反思均衡法的两条判准;相比于强调法官具有裁量权的理论而言,以该主张(法律理论)来解释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似更为合理且正当。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德沃金在本部分(正面回应)的论述并非倚重法律原则,而是转向了其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权利,因为在裁量案件的过程中,法律原则有时可能势均力敌,论者各持相反意见,此时自由裁量权关涉的不是依据原则裁判,而是案件当事人双方各自宣称有权利获得胜诉之判决,并否认法官有判决对方胜诉的自由裁量权。同样,下文讨论的唯一正解理论,也是围绕“权利”展开的。
德沃金的“唯一正解”论
(一)“正解论题”的权利理解进路
在德沃金诸多原创性的法律理论当中,最具争议的应当包括正解论题(right answer thesis),即复杂的法律及政治道德问题,通常有唯一正确答案。“正解意味着答案是准确的,是确然存在的,即使在法官裁决案件之前也是如此”,即使在疑难案件中亦存在唯一正解。
由于正解论题的内涵令人惊异,甚至有悖于一般人的法律常识,至少司法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法律领域的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解,所以,该理论需要探讨的首要且核心问题就是法律问题是否确实存在唯一正解。
质疑正解论题的一种具体观点可以表述如下:(复杂的法律和道德问题)有时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而是存在好几个答案;法律问题往往无唯一正确答案。针对此种观点,德沃金进行了长篇回应。
首先,德沃金对支持“法律问题无正确答案”这一观点的论据作出了类型上的区分。第一种论据是“务实性论据”,它主张:即使原则上存在着一个正确答案,但说法官有义务去发现这一正确答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的答案并不比其他人的答案更正确;而且,法官对案件的意见如同美学家对艺术品的欣赏,是非常主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而比起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没有什么能担保法官的意见为真。”第二种论据是更加强有力的“理论性论据”:在法律案件特别是疑难案件当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享有特定法律或政治权利存有争议,那么“他享有这项权利”这项命题就不可能为真。
德沃金对“务实性论据”的具体反驳如下。起初,他区分了三个问题:(1)在疑难案件中,如果所有的事实都毫无争议,那么理智的法律人是否还会对当事人享有胜诉的权利产生争议?(2)在所有的事实都没有争议,如果理智的法律人依然意见相左,那当事人是否仍然享有胜诉的权利?(3)如果另一组法官对某疑难案件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判决,那么执行一组特定法官对该案的判决是不是合理与公平的?
然后,德沃金根据这对这三个问题的区分给出了以下三点反驳务实性论据的理由:
(1)“务实性论据认为,第一个问题的肯定答案,排除了第三个问题的肯定答案,即使给予第二个问题肯定答案,也是一样。”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假如没有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即在某疑难案件当中当事人有胜诉之权利)作为支持,就不可能得出对第三项问题的肯定回答(即执行该判决是合理且公平的),也就是说,第二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第三个问题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现实的司法实践当中,有很多疑难案件已经执行了判决,而且也是公正的,那么反过来思考,我们就不能说,在这些案件中,当事人没有胜诉的权利,因而也不能说这项疑难案件没有正确答案。
(2)这一点理由涉及到判决的权威性问题。即使某项法官的判断有疑义甚至可能出错以至于无法证明其正确性,但我们也应该让法院做出这项判决,因为这样做要好过将该案件交由其他机关来处理。
(3)务实性论据认为有争议的权利在判决当中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一点是:在疑难案件之外的简单案件当中,我们可以接受权利命题,也可以接受法律问题存在正确答案,但这并不能说,在疑难案件当中,我们就必须认为没有正确答案;亦即权利争议并不代表没有权利,答案有争议并不代表没有正确答案。
德沃金对于理论性论据的反驳则更为犀利。首先,他提出了反驳“无正确答案”命题的一种现实层面的论据,即如果某人(假设是哲学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法律专业训练,他/她也会作出之前认为是错误的裁判,也会像现在的法官一样笃定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答案;也就是说,法官心中的正确答案受到职业的影响而在实质上异于哲学家和其他非专业人士视角中的正确答案。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反驳论据。德沃金将上述理论性论据的视角进行了分类,一种是法律事业的内部视角,另一种是法律事业的外部视角。
若从法律事业内部的视角来审视此论据,“无正确答案”这项观点会遭到以下反驳:
(1)那种类似于“这些相反命题均不为真”的判断(也就是无正确答案之判断)可以称其为“平手判断”(tie judgment),而平手判断是处于法官心中的“信心量尺”的中心那一点,它与位于刻度尺的两端的判处一方当事人胜诉或败诉的判断地位相当,因而也只是三种判断中的一种。同时,由于平手判断是在说明另外两种判断为假,所以,它其实就是在自认为自己是正确答案,因此,“无正确答案”这种判断本身就是“正确答案”。
(2)上述平手判断也是法官个人做出的,因而就包含了一定的主观性,而不是一种客观结论,因此,它就并不比另外两种判断更具有优越性。换句话说,无正确答案这一判断只是判断的一种,而并不比其他的判断更具有说服力;法官“认为”某案件无正确答案和此案件“确实无疑”无正确答案是两回事儿,前者只是法官自己的主观判断。当然,在一场赛马比赛当中,我们可以设立如下规则:如果摄影机拍摄的照片模糊以至于无法判断哪匹马赢得比赛,那么就可以推定那些马是平手。在这个例子当中,“机器不能判断赢家”与“没有赢家”就是同一回事。但是,在法律事业当中没有也不允许存在此类规则:某些法官做出平手判断,那么这起案件就真的是平手案件,亦即就真的是无正确答案。相反,某些法官做出无正确答案之判断并不能说明就真的没有正确答案;即使法官真诚地认为无正确答案,基于其职业责任,也必须做出双方当中有一方胜诉的判决,而不能像赛马的例子那样,随意宣判没有当事人胜诉或撒手不管。
(3)“某个案件属于平手,因此在这项事业之内没有正确答案”这种说法会产生争议。因为,“无正确答案”这项命题本身的使用范围就不确定(比如是适用于某些案件还是适用于整个法律事业中的全部案件)。不能说某些甚至少量的疑难案件是平手,就推出这项事业内部全部的疑难案件都是平手,因而完全没有正确答案。所以,在法律事业当中,就算某些疑难案件“没有”正确答案,但很多疑难案件依然“有”正确答案,因此,“无正确答案”这一命题因其范围问题而无法自圆其说。
(4)在一种比较原始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制定法和判例都很贫乏,法律的复杂程度很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平手案件的“事前可能性”很高;但如果法律体系足够复杂,以至于在法律事业内部有一项基本规则,该规则规定,法官不能做出平手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产生平手案件,因而也不会“没有正确答案”。(而且,就算目前的法律体系不够复杂,但未来的法律体系可能会足够复杂,以至于任何法律问题都有正确答案)。
对于该观点,理论性论据可能会反驳道: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复杂的法律体系,以至于不给平手案件留有空间;因此,必须要考虑平手案件的事前可能性。倘使如此,理论性论据还是输了,因为此时它已经承认不是所有的疑难案件都会是平手案件(因为这里的用词是考虑出现平手案件的“可能性”,而不是“绝对”),因而也不是全部的疑难案件都是“无正确答案”的。
理论性论据还有可能从法律事业的外部对正解论题进行批判,德沃金将此类批判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某人(假设是一位哲学家)从另一个不同于法律或司法事业之事业的内部对法律事业内部的疑难案件有正确答案的观点进行批判。在这类批判中,哲学家构想了一项法律事业,其中规定了以下规则,而根据这些规则,在“任何”疑难案件中,判定原告或被告有胜诉权的法律命题都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因而,在任何疑难案件都没有正确答案。但是,德沃金分析道,哲学家构想的这种法律事业和真实发生在英美国家的法律事业是两回事,因为后者的司法事业当中显然没有这类似的规定,法官也必须判定两造中的一方享有胜诉权,因而哲学家构想的这种事业无法应用于法律事业。
第二类是哲学家从一种世界真实性的角度来批判疑难案件有正确答案的观点。从这种角度出发,哲学家描述的不是一种个别的事业,而是所有的事业都必须符合“客观真实”。哲学家似乎是在说,在客观真实当中,当事人可能享有权利或负有责任,但法官根本无法发现这些独立于法律世界的真值条件。但是,德沃金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享有这些权利?主张真值条件独立于现实地法律世界是一种危险的说法。
的确,笔者认为,主张有独立于法律体系的权利的客观事实难道不更像一种形而上的空想吗?这也可以构成对自然法的一种批判,即认为在实在法之上还有一种正义或普世的法,这难道不是一种空想吗?而且到底存不存在脱离任何大前提或语境的普遍正义呢?我们似乎在某个前提——如既存的法律——之下谈正义更着边际一些。在这里,可以说德沃金是反对“自然法”之部分要义的。通过对以上务实性论据和理论性论据的拆解,德沃金暂时捍卫了自己的正解论题的“正确性”。
然而,笔者认为,德沃金的这一命题及围绕它展开的讨论,与历史哲学当中何为“客观”以及能否客观地把握历史(唯一的)真相的讨论颇为相似,因为前者亦在探讨法官能否找到法律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因此,以下将尝试移借历史哲学中的相关探讨来检视德沃金的这一命题。对于何为“客观性”这一问题,历史学家梅吉尔(Allan Megill)认为客观性分为四种:“绝对的,指的是在如实地表征外在对象这一意义上的客观性;学科的,指的是能够在特定的学科共同体内部就客观性标准达成共识;互动的或辩证的,指对象或客体是在主客(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互动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从而认识者的主观性就成其为客观性中不可离弃的成分;程序的,指的是依靠研究过程中不带个人色彩的方法或程式而达到的客观性。”根据此种分类,又从对上述两种论据的反驳的思路可以看出,德沃金“法律问题存在唯一正解”的命题侧重于上述第二种语境,亦即是在法律事业或法律学科内部认为法律问题存有唯一正解。
但是,若将德沃金的该命题运用到第一种语境则会显出其不合理性,因为在此语境下,笔者认为,没有唯一正确答案:判决(至少在疑难案件中)依赖法官如何解释,而每种解释都是法官固有观念及理论框架(主体)和具体案件(客体)互动的结果,亦即解释当中掺杂了主观性的成分,因此我们无法断定何种判断或答案为“真”或正确。此亦笔者所认为的德沃金的唯一正解命题之局限所在。
(二)面向权利“实践”的“正解论题”
正解论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宣称法律问题存在唯一正解的主张到底有没有实践上的价值?与之相关的批评来自穆泽尔(Stephen R. Munzer):除非能够在原则上假定正确答案或当事人胜诉的权利预先存在,否则将某种答案或权利解释成唯一正解,是没有实践上的价值和实际利益的。
穆泽尔的这种观点是对权利的错误理解,甚至可能会导向判决理由的虚无主张。德沃金指出,某人享有特定的政治权利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仅凭它自身就能够证立司法判决;认定某一答案是正确答案本身就是判决的最佳理由。如果将穆泽尔的上述观点运用到道德领域的具体情形,将更能体现出其对权利的虚无倾向。举例来说,假设C因为粗心大意而对D造成了人身伤害,D自然有权向C主张赔偿损失,C也承认D的这项主张,但C又旋即指出,这只有学术上或认识上的价值,而无法为要求我真实地做出赔偿而提供证立,因为D的权利与我的责任都存在争议,因此无法要求我在事先没有意识到D的权利的情况下进行赔偿。
但是,除了上述错误理解,德沃金经过深入剖析指出,穆泽尔的观点还存在着关于权利的更一般性的错误。在普通的案件当中,法律权利能够经由法律人凭籍三段论而从法律文本中推导得出,这一事实会引诱人们得出以下两个错误的结论:所有的法律权利都存在于法律文本或书籍当中;即使无法查明这些权利,或者说当前的法律文本并没有显示某种权利,那它们也一定存在于当前不可见的秘本(secret books)当中。所以,受以上两种结论的影响,穆泽尔的观点也在实际上假定,权利必须存在于实在法律文本中,或者说是存在于目前不可知的秘本中。但是,这种假定或者说法律人的认知倾向将导致思维的僵化,因为它会将我们的思路仅仅限定于文本之中。
德沃金认为,法律问题特别是司法裁判问题,不应该仅仅是文本问题,还更应该是原则问题,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当事人之所以享有权利,不是因为文本的规定,而是出于某种公正性,而且这种公正性基于有力的论证与说服,而非像秘本那样的空想。
此外,如果我们拘泥于文本,那可能走向为邪恶政权之存在提供正当性以及为邪恶行为提供注释的极端,比如,在纳粹的政权统治下,法律条文很充实,但公民仍旧没有权利,但根据上述两个结论,却又是合理的,因为法官的判决和政府的行为都是依据法律文本作出的。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依据法律文本治理国家和法治(rule of law);毕竟“相比于法律文件之治(the rule of legal texts),法治是更高尚的理想。”
透过上述德沃金对穆泽尔观点的前提假定的批判,笔者发现德沃金在批判某种具体观点时会运用一张方法,即挖掘出这一观点背后的前提假定或预设,然后对之展开批驳,既然作为立论基础的前提假定或预设站不住脚,那观点本身就缺乏合理性。在A Matter of Principle中,他对“民主要求政治性决定必须交由立法机关而非法院作出”这一观点进行批判时,亦充分运用了此种方法。
余论:“定位”德沃金的两难之境
(一)自然法学家的“标签”
对于德沃金在法学家“序列”的定位,法学界的一般共识为他是一名自然法学家。但是,笔者在研究其著述的过程中发现,德沃金有许多思想展现了他异于甚至是反对自然法的一面。
首先,德沃金的思想及论述风格有一个特点,即含有强烈的针对概念进行分析与分类的色彩。他的作品中的某些部分,其分析性丝毫不亚于作为新分析实证法学界执牛耳者的哈特。美国法理学界的专业人士也认为德沃金的作品带有此种概念分析的印记:“分析哲学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严格地、符合规矩地进行概念讨论。为了阐明命题,分析哲学家仔细进行论证。在思考权利时,罗纳德·德沃金运用的正是这一方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仅因德沃金批评法实证主义就将其归类为自然法学家。
其次,当德沃金在为其正解论题辩护时,他明确反对那种认为权利或责任存在于超越法律世界的客观真实世界当中的观点。而且,在分析穆泽尔无正确答案之主张的错误根源时,他举出秘本的例子,并说明,“当无法从书本中推导得出时,权利就一定存在当前法律人接触不到的某种秘本当中”这种主张隐藏在“‘非实证主义者必定相信所谓自然法,人们认为那就是天上秘本的内容’这项前提假定背后。”但他明确反对这种秘本理论:“秘本图像无法适切地说明为什么人们能够享有法律权利。”
依上述论据,笔者目前认为,不宜简单将德沃金归为自然法学家之列。
(二)“解释”抑或“描述”?
在《法律的概念》一书的后记中,哈特认为,其自身的理论是描述性的,而德沃金的理论是解释性的,因而也包含了部分评价性。但是,笔者认为,德沃金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描述性的(至少其早期著作《认真对待权利》中是这样的),因为对于他提出的法律原则理论、权利命题乃至唯一正解命题,都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在试图更合理地描述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现实与司法实践,德沃金对自己的这本著作亦作出过类似的评价:“我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提出的反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论据,着重于审判现象学”。
不仅如此,德沃金自己也在这本著作中提到过,他的理论——至少是权利理论——并不是为司法实践提供一种应然性判准或指导:“我费力地强调,我不打算提供什么改革方案,而只是针对我们都晓得的、法官的所作所为提出更好的特性描述,它(注:是指权利命题)之所以更好,是因为它让我们能够了解,许多熟悉的政治性与概念法理学问题不是司法裁判的现实造成的,而是源自于我们那招致误导的、描述这些事实的方法,就像我们因认为Jourdain先生念了无韵诗而栽进的概念性困扰。”
论及“解释”,笔者发现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与哲学诠释学似存在微妙的关联。德沃金在《法律帝国》第二章以注释的形式详尽阐述了“对话性解释”与“建构性解释”(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并提到了狄尔泰、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著作,并说明自己的建构性解释理论与这些论者相关理论的不同之处。故如下问题是值得探究的:德沃金在多大程度上受影响于上述三位学者的论著,以及他们四位大家的有关解释的理论存在哪些差异?
最后,无论是“自然法学家”抑或是“解释性理论”,都无疑明确地彰显某种标签属性。于定位而言,标签明晰简洁,有时是切近这位学者及其理论的不二法门,但迅疾识别的背后,因概括剪裁的需要就可能遮去学者及其理论本身的多元属性。相较于标签与多元属性的两难之境,不变且更重要的可能是围绕学者及其理论本身具体的阐释与再阐释,不断思辨“写作”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高忠义译,商周出版2018年版
[美]詹姆斯·哈尼克编:《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榆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美]朗诺·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孙健智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
[美]斯坦利·I.库特勒编著:《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朱曾汶,林铮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美]罗纳德•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德沃金复旦大学讲学纪要》,徐品飞、张嶂、肖明整理,载《清华法学》,第1卷2002年第1期
[美]布赖恩·H.比克斯:《牛津法律理论词典》,邱昭继、马得华、刘叶深、冉杰、鲁强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许杨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美]阿兰·梅吉尔:《客观性的四种涵义》,转引自彭刚:《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